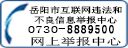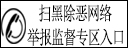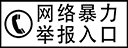今天是2023年1月8日,农历是腊月十七,天气晴暖。
写下这句,就坐在太阳底下,我无法描绘这温暖。
就一直暖暖地,空白着,接电话,打电话,回信息,转信息。
下午阳光从阳台移走,看到小师弟林沙说,“今天我们就喝点非零度可口可乐送送他吧”。起身,去楼下星巴克点了一杯馥芮白。我的刘恪老师,他喜欢可口可乐,最近几年因为身体的缘故转向零度可乐,他努力地想好转。他也喜欢咖啡的名字,曾用卡布奇诺、玛奇朵、香草拿铁指代朋友们,他喜欢让我喝馥芮白,就是觉着这三个字看着好看,读起来好听。
12月27日,新赞师弟电话说,刘老师住进了医院,进食困难,排痰困难,白肺,住不进ICU。这十余日,我时不时地祈祷他能战胜此疫,时不时地又想他还是不要受这份罪了,时不时地接到他朋友或学生的电话问询情况,我无法回答,我也去不了岳阳,惟是怔忪,惟是失神。
今晨六点多,收到沈念的信息“非常遗憾,刘恪老师凌晨去世了”,收到新赞的信息“刘恪老师凌晨四点走了”,木木地转给了几位近日问询病情的师友,那两行文字仿佛就是两行文字,一整天我都在拒绝它们。
傍晚时候,河南大学文学院的老师嘱说,写一点纪念刘老师的文章吧,我说我试试。九月份时候,河南小说家墨白想让我写一篇文章谈谈刘老师的理论贡献,我说我尽量。其实我从心底里抵制这样的文字,仿佛只要不写,我的老师就还有漫长的时光。7月中,刘思谦先生走了,12月末,刘增杰先生走了。孟庆澍老师说,他们连离开都相互招呼着,搀扶着。现在,刘恪先生也走了,孤独地弃绝了这卑微的生活。
我热爱的老师接连离开,我找不到词语描绘这感受。
……
第一次去听刘恪老师的课,是在2009年春天。那是研二的第二个学期刚开学,一次课后听到两位同学说,刘恪在给本科生上现代小说理论课,就问了上课的时间与教室。按时去蹭课,坐在第一排的左边,随意瞥了一眼正在看讲义准备板书的老师,一眼下去就乐了:一件砖红色的棉外套,里面是一件法兰绒蓝绿格子衬衣,衬衣领口露着灰色秋衣,衬衣秋衣扎在牛仔裤子里,蓝色牛仔裤腰处露出一圈灰色秋裤腰,高高的,色彩比较撞。秋裤腰露在衬衣外这种装束,我见得不多,忍不住咧嘴笑,被刘老师一眼瞥见,那姑娘你开心啥子,我随口胡扯老师你今天看着真精神哦,他哈哈哈哈一串大笑,骂道拍马屁的家伙。
那节课讲的“风景”,刘老师用他那湖南话与北方话挼搓的普通话,神采飞扬地侃着“风景”概念在中西传统中的词源、内涵与流变。课后,我的两位同学抱怨这个写小说的刘恪真是不会讲课、一个概念说了两节课还没说完,他俩后面就再也没来。我却听得兴致陡起。别人总说我性子张扬,其实那多半在掩饰社恐,我自小就是绕开老师走,节日问候都需做一番心理动员,那天却鬼使神差在课后去搭讪,嘻嘻哈哈说老师我来帮你收收东西送送你吧,他上课带来一包书,课堂中提到了就举给学生看,沉甸甸的一大包。
那之后,放学经常一起走,刘老师,王向威和我。刘老师住在苹果园的河大老家属院,我租住在苹果园的老年公寓,他回家要路过我家,路上多是听他们俩谈论这个书那个书,十多分钟到我家路口,我回家,王向威继续跟刘老师走去他家吃饭。那会儿特别佩服王向威,他读了很多书,书名我都不知道。
学期结束时,刘老师终于不想忍我了,抓我跟着他们去淘书,七月的开封路面热得烫脚,有时候坐着一块钱的小公交到一个胡同里,钻进一个石棉瓦的棚子房里,一进去我就哈气说这会中暑的,他面无表情应一声一会儿买个冰棍。有时候去诗云书社,他老人家进去就生根,半天不动身。带我混了三个月的书店,刘老师终于发现我基本不买,终于忍不住问原因,我认真模样着回一句不知道买啥,其实是不好意思说没钱。那以后,他开始送书,一包包的,吼吼着李海英你给我打字,我给你买书,这买卖你不亏的。
这桩买卖一做就做到了博士毕业。我在博士毕业论文的致谢里说:“首先感谢刘老师懒得使用电脑这一习惯,使我有机会帮助他打字、编辑或整理文稿,从而有机会从他那里获赠了近百本图书,其中的许多诗歌理论著作都是既不好借倒也不容易买到的。每当我想表示感谢时,刘老师就哈哈大笑,礼物嘛,老头子摆夸富宴吔!(可我没得夸富宴回请啊。)然后更应该感谢的是刘老师这些年来的教导,从读研究生始,我曾先后跟随他完完整整地上过《小说理论》《美学》《文本分析导论》《文化研究》《文学理论关键词》《小说发生学》等五六门课。”

刘恪老师在自己的研讨会上则说:“……李海英肯定很痛恨我,因为我一写完就要打出来,一打了后面就得要校对,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但是不搞完我又不放心……我是用钢笔在大稿纸上书写,你想从早晨六点半写到晚上的时候,我都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,僵直了,倒下身体后才能扭动脖子,再躺床上面,哦,可以放松了。我的眼睛现在老花了,已经有点厉害了。那么写完了以后呢,我就去找耿占春,路上经常看到是三四个影子在那边晃,头也是晃的,在那边晃,一直晃到诗云书社了,要打印了就晃到李海英的楼下,我肯定是要把这事情干完。没有考虑到我要死亡或是怎么着,没有。……基本上我不能休息,她也不能休息,那没得说,我写一个字,她就得打一个字。所以呢,这个李海英也占了我不少便宜,我那些诗歌理论书、诗歌书,我都权当割我肉一样地给了她,自己都没有了。”
这件事情的始末是,礼物交换开始不久我就发现,这个刘老师是只老狐狸,送书给朋友给学生那是他的挚深爱好,一堆师长跟我讲刘恪曾经怎样给他们送书怎样寄书、不让他送他难受呢。于是我开始提出礼物交换的内容应该重谈:打文稿,换新课,书爱送不送。2005年,刘恪老师与萧开愚老师作为引进的作家类人才入职河南大学,学院没有安排他们带硕士研究生,刘恪老师分在文艺学教研室,萧开愚老师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。也就是说,刘恪老师没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课程,我只能去文艺学专业旁听,难得的是,那会儿河大老师上课有些自主权,所以我可以猖狂地“点课”。刘老师又是哈哈哈哈一串大笑,骂着鬼家伙终于长点儿脑子了,于是专为我设计了三门课程。
说句没良心的,其实别的学生要求,刘老师也一样会开讲。略熟悉的人都知道,刘恪“热爱”年轻人的学习热情,“热爱”年轻人初显的才华。我记得有一天夜里11多钟,忽然接到他的电话,第一反应是出了什么大事儿,唬得我噌地就去换鞋子,结果听到电话里很热闹,乌拉乌拉的一边喧声讲,扑通扑通地一边迈大步,听了两分钟才明白他见到了一个叫阿威的孩子,诗写得好,谈吐好,人长得也好……赶紧记住喽。慢慢地,我知道了沈念、舒文治、丘脊梁、郑小驴……天天夸赞他小同乡,知道了张运涛、王红伟、魔头贝贝、智阿威……被逼去记着我同乡。早些年,利诱我给魔头贝贝写个评论,他俩没有任何交情,他就是要做纯粹支持,也威逼我决不能给谁谁谁给某某某写评论,顺手拉一串黑名单,顺手给的理由总是:你得有批评家的责任。
所以,我说的是真心话,刘老师说的也是实情。刘老师待朋友待学生,经常是好到不可理喻,但也常有粗枝大叶,为了不听他啰嗦,我有时是靠布洛芬撑着给他赶稿子,还一天几个电话问进度,我就会怒吼。偶尔还耳根子软,办些破事儿,比如有次一个学生想进入他的“后记”,他就让那个学生打了一两万字稿子,结果错误太多,还不让我重新打一遍,那样他就没法把人家写进后记,费了我整整两天时间去校对修订,他一脸坦然:我知道你在刨我家祖坟。
这些年总有人问我,你是现当代专业的,怎么像是文艺学科班,河南大学文学院抓史料疯狂,抓理论也疯狂?我就会很得意,因为遇到了那么多好老师,我的老师刘增杰先生和刘思谦老师,七十多岁的年纪,一个盯着我去苦读原始文献,一个告诉我要勇敢肆意;我的硕导张先飞先生,严格到作业的文字排版都得是最好看的,耐心到每周都会变着法子鼓励/批评/安抚一次学生,不是他一次次无底线地夸张我的“才华”,我绝无勇气报考博士研究生;刘恪老师和萧开愚老师,展开的是于我而言全新的视野、思维、感受力,让我慢慢理解了敏感、不确定、疼痛的合理;后来我的博导耿占春先生,开阔、澄明、宽厚,呵护个性的自在状态。
当然,也总是很黯然,博士毕业时,刘老师说了两件事情,一是已经给我补了三年西方文论,应再补三年中国古典文学,这样走路才会稳当;二是他计划写一部大长篇,将多年的小说出一套文集。
这两件事情都未成行。
……
命运,真是一个古怪的命题。
病后与病前,截然的两种情态。曾经那么健康的一个人,耿老师说刘恪能把犯了腰椎痛的萧开愚老师一口气背下五楼,新赞说刘老师一口气能做五十个俯卧撑。这些我没见到,我见到的是书也好、西瓜也好、箱子也好,都是他自个拎上五楼的。我听到的是,他吹牛说自己活到八九十岁没问题的,因为他大伯、他父亲就是活到了八九十岁还能吃能喝的。
大约在五年前,六十五岁前,两种主要的病症便显示出来。我记不清是2017或是18年前后了,先是在开封的一位老诗人赵中森先生打电话,说刘恪的鞋子看着很不合适,走路不稳当,他看着心里很不是滋味很担心。赵中森先生是刘恪老师到开封后“再发现”的一位作家,赵老师儒雅、温润、挺拔,字写得好,拍照也好,刘恪老师的一些好照片就是他拍的。还“再发现”了一位在郑州的小说家“老张斌”,盛赞其语言之精妙,张罗着给他出书、开研讨会、写评论。
我去北京看望他,说已经诊断出帕金森了,有些焦虑,又说及时治疗、积极锻炼应该问题不大,每天走一万步,也在努力吃一点肉类。带我去人大附中看望小说家王俭印,然后就一直忙着倒腾手机、傻笑,王老师嘿嘿:你刘老师在谈恋爱。我们一起去附近的商场买鞋子,逗他:你在小说里写给女朋友买耐克,自己没穿过,很是怨气,咱今天平了这怨气,学生给你买一双,再加双袜子。他有些黯然,配合着试穿。我没心没肺地开玩笑,想哭,不敢,想骂,不忍。那几年,他钱总是不够用,各处跑来跑去的,挣的还是不够,大长篇也没时间开始。
前列腺炎缠绵了好些日子,从北京回到开封,计划在开封做手术,因为医保在开封,我拜托侯运华老师帮忙找了一个有名的专家,也请好假准备回去照顾他。咨询了一些朋友之后,他决定不做手术了,冬天的时候返回北京。19年的冬天,感谢清华大学的诗人西渡大哥,他举办了闻一多研讨会,会后去看望刘老师,新赞特意交代我要给刘老师收拾收拾屋子。没有记错的话,那一天是冬至,一川老师也讲好要来,我一大早过去,收拾到快中午时分,总算刨出一个地方可以坐人。那个时候,刘老师说话已经有些挺听不太明白了,走路也开始颤巍,一川老师给他买了好几个拐杖。午饭时,一川老师尝试跟他谈后面的事情,但他拒绝回应。再后来,《现代小说技巧讲堂》再版,我买了几十本给他,方便他送人,签名已经歪歪扭扭。
这期间,他强撑着想要装修郑州的房子,居住在郑州的小说家、诗人尹顺国帮忙做完了全部的装修。去开封拉书还是家具,从椅子上摔下,头破血流,我在昆明,只能急呼陈尧,陈尧二话不说就赶往医院。今年春天开始,我几乎不能联系到他,五月去岳阳探望,诗人路云也来探望,带刘老师去走了一趟岳阳楼,在洞庭湖边喝了杯银针白毫。这许多情义,唯有感谢。
此刻是1月9日05:50,亲爱的老头,我在远方给您守灵。回想了这些年,迟钝昏沉地写了这些话。
6点钟,天要亮了,该出发了,到岳阳。
女学生不能给您抬棺。但我会在心里默默说:旗帜轻灵地变成翅膀……
作者介绍:李海英 教授,文学博士,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,研究方向为中国新诗研究、西方现代诗歌研究。目前主要从事诗歌批评及研究,在《诗刊》《诗探索》《新诗评论》《星星诗刊》《扬子江诗刊》《扬子江评论》《上海文化》《江汉学术》《光明日报》《南方文坛》等刊物发表文章70余篇,偶有文章被《新华文摘》转载。出版专著《未拨动的琴弦——中国新诗的批评与反批评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),《伟大的尘世之诗——华莱士·史蒂文斯诗歌研究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)。